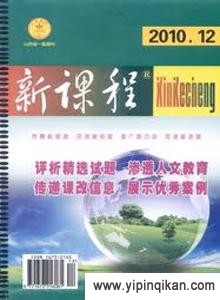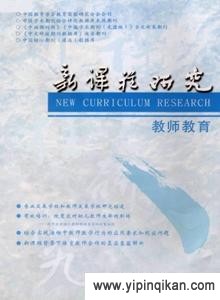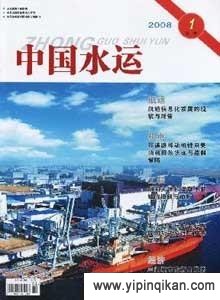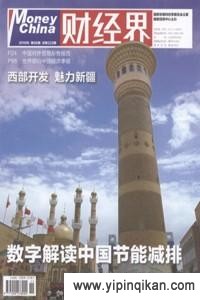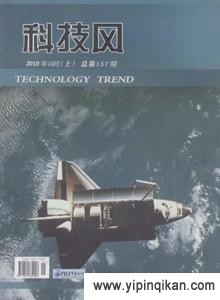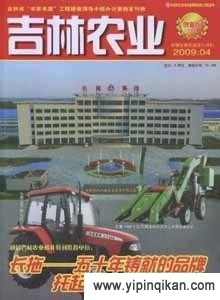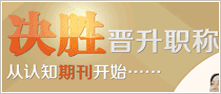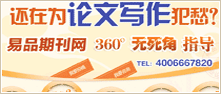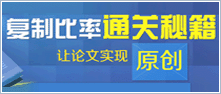论‘精神的底子’语文化(一)
“精神的底子”之说是钱理群教授在其著名长文《以“立人”为中心》提出的,①曾受到广泛认可。可此后不久,薛毅教授就发出警示:“当钱理群说这些内容符合青少年的特征的时候,他没法证明它们符合语文教育的特征。”“新语文观念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它自身走向了僵化和空疏,停滞为一种口号,一种标签”——他的这个警示不幸被而后出现的“非语文”“泛语文”现象所证实。他更深刻地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从语文教育本身而言,‘精神的底子’如何内化为语文教育自身的目标?应该使‘精神的底子’语文化,而新语文观念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文化毕竟不是语文,文学也毕竟不是语文。所以,问题应该是,如何在语文具有文化性、精神性的前提下,使语文寻找到自身的位置。”②对薛教授的这个“‘精神的底子’语文化”问题,李海林教授称赞为“新语文的‘语文性觉醒’”,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十分悲观:“这是一个十分艰深的理论问题,目前的学术积累还不足以解决这样艰深的理论问题。”③
“‘精神的底子’语文化”这个问题,的确是语文学科一直没有解决的“十分艰深的理论问题”。细想想,60多年来语文教育出现的和争论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精神的底子”没有“语文化”造成的。这个“十分艰深的理论问题”该是解决的时候了,目前的学术积累也到了有可能解决这个“艰深的理论问题”的时候了。
一、必须彻底转变认识语文的角度和研究语文的方法
“语文化”就是“知识化”,而“知识化”必先从“命名”开始。《墨经》云:“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这是说,事物所以这样,与人认识事物的角度,与人用来进行认识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不必相同。可是,在这两方面,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变:都是站在“人”的角度,都是使用传统“主体—客体”认识论的方法来认识语文,而不是站在“语文”的角度,运用“本体论”(“存在论”)的方法来认识语文。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必然导致“命名”(使用的概念)的大不同。
站在人的角度,用传统认识论来观察语文,就得出“工具性”“思想性”(后来是“人文性”)的命名。站在语文的角度,不强行给语文命名,而让语文自我显现。本体论又叫做“现象学还原”。现象学有一个纲领性的口号叫做“面向事情本身”。“面向事情本身”就是让事情、事物自我显现,人不再另外予以命名,而只是“描述”。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说明,而仅仅代之以描述。”“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④海德格尔所探讨的就是“语言作为语言”的语言本身:“我们并不想对语言施以强暴,并不想把语言逼入既定观念的掌握之中。我们并不想把语言之本质归结为某个概念,以便从这个概念中获得一个普遍有用、满足一切表象活动的语言观点。”“我们要沉思的是语言本身,而且只是语言本身。语言本身就是语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⑤他认为语言本身是关于存在的“道说”和“显示”,语言本身的“道说”才是“思”的语言,“诗”的语言,才是“此在的本真的居所”,才是“可思性的庇护之所”。“人之能够说,只是由于人归属于道说,听从于道说,从而能跟随去道说一个词语。”“显示着的道说为语言开辟道路而使语言成为人之说”,“成为我们人之所是,我们人始终被嵌入语言本质中了,从而决不能出离于语言本质而从别处来寻视语言本质”。⑥
读了这两位伟大哲学家的论述,我们才明白:就语文(语言)的能指来说,“言”就是“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比如“工具”);就语言的所指来说,言所表达的就是“意”,“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比如“人文”)。所以,将语文定性为“工具性人文性的统一”,就是人为地“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就是“对语言施以强暴”,就是“把语言逼入既定观念的掌握之中”——这样多此一举、出力不讨好的命名,遮蔽了语文的本体——所以语文成了“非语文”。而“言”和“意”,才是语文的“常名”,才是对语文(语言)本真的“描述”,才是语文(语言)本身的“道说”和“显示”,才是“思”和“诗”的语言,才是“此在的本真的居所”——人存在的家。它不仅能“成为人之说”,而且能“成为我们人之所是”,还能让“我们人被嵌入语言本质中”,使我们“不能出离于语言本质而从别处来寻视语言本质”。
二、必须从形而上本体之道的高度来观照、审视和研究语文
虽然“言”和“意”可以使我们“不能出离于语言本质而从别处来寻视语言本质”,但它们只是语文的“命名”而已(只是“不能出离于”,而非“就是”),要寻找语文真正的本质,还应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深究。王国维说:“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不仅如此,还要“必求诸”被称为“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语)、“科学的女王”(康德语)、“至圣的神”(黑格尔语)、“科学皇后”(胡塞尔语)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指超越于具体事物之上的不变本质、本原等规定根据的学问。它是一种超越经验之上的追问,是一个属于本体论的问题。本体论作为世界终极存在的追问,也不属于经验世界而是一种超验世界,所以它与形而上学是同义语。《周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形而上学、本体、道,可以看作是同一个问题。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40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42章)言意关系是语文之“母”、之“本”、之“虚”、之“无”,各种言语作品是语文之“子”、之“末”、之“实”、之“有”。言意关系在空间上无边无际,无形无象,不能直接被人感知——“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老子》14章);它在时间上无始无终,但却运转不息——“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老子》14章),“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25章)。言意关系之道是语文之“体”,语文之“共相”,各种言语作品是语文之“用”,语文之“殊相”。“体”而被“用”,就不存在差别、异化问题,因而有“体用不二”“体用一源”之说。由“殊相”到“共相”,这是逐渐抽象化、概念化、逻辑化的过程;由“共相”到“殊相”,这是客观化、具体化、形式化的过程。“体-用”关系和“共相-殊相”的关系,就是朱熹说的“理一分殊”“月印万川”的关系。言意关系之道作为语文之“体”,语文的“共相”,语文的“理一”,一旦被“用”,被“分殊”,就像“月印万川”一样,成为各种各样的话语和作品(殊相)。这些都属于认知范畴的思考过程,都具有知识性。
维柯认为,哲学的概念是凭思索和推理形成的,“哲学语句愈升向共相,就愈接近真理,而诗性语句却愈掌握住殊相(个别具体事物),就愈确凿可凭。”⑦康德说:“形而上学便是知性世界的知识形式。”⑧我国学者冯达文说:“‘本体论’面对的问题,才是经验知识与经验世界的问题,它涉及的,是关于经验世界的真实性与经验知识把握世界本真的可能性问题,惟是才可以放置在知识论或对知识论反省的立场上予以考察。”⑨言意关系就是语文的“接近真理”的“共相”、“形而上”的“知识形式”和“本体”,就是语文的最高的知识形态。
对于一种知识而言,如果没有本体论的建构,就缺乏形而上学的思维,就无法超越经验事实和实践理性,就没有一个统摄整个知识体系的东西,因而就难以做到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论述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体论是知识的灵魂,一种缺少本体论建构的知识,就像是一座没有神的寺庙。欧阳修《易或问》云:“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学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后知学《易》矣。”朱熹《四书集注》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有了言意关系理论这个语文最高形态的知识,几十年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的“肢解”(于漪先生语)和“钟摆”(李维鼎先生语)痼疾将一去而不复返,“语文:魂兮归来”(钱梦龙先生语)的梦想必将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言意关系作为语文的形而上之道,与古代“文道之争”中的“道”是不同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以文传道”的“道”指的是“道统”,即圣人之道、孔孟儒家之道,亦为人文思想和精神。其次,“文与道俱”“文与道合”之说中“文”“道”好像是一体的,其实暗含着二体论,其中的“道”指的也是人文思想和精神。上面六说之“道”(属于道德形而上,是实践论的本体论,讨论“所应是的东西”)与语文的形而上之“道”(属于自然形而上学,是本体论的认识论,讨论“所是的东西”)一直没有被分辨清楚,这就是“文道之争”千百年来绵延不已、难成定论的根本原因。倒是朱熹的“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元代中后期的许有壬主张的“文与道一”说(《至正集》卷七十一《题欧阳文忠公告》)和清代刘熙载的“艺者,道之形也”说(《艺概序》)值得肯定。他们所说之“道”皆为“理道”(属于自然形而上学),但是他们都没有揭示这个“道”独特而具体的内涵(即“言意关系”),只是泛泛而论罢了,所以在文论史上不大为人所知。
未完待续...
- 认准易品期刊网
1、最快当天审稿 最快30天出刊
易品期刊网合作杂志社多达400家,独家内部绿色通道帮您快速发表(部分刊物可加急)! 合作期刊列表
2、100%推荐正刊 职称评审保证可用
易品期刊网所推荐刊物均为正刊,绝不推荐假刊、增刊、副刊。刊物可用于职称评审! 如何鉴别真伪期刊?
都是国家承认、正规、合法、双刊号期刊,中国期刊网:http://www.cnki.net 可查询,并全文收录。
3、八年超过1万成功案例
易品期刊网站专业从事论文发表服务10年,超过1万的成功案例! 更多成功案例
4、发表不成功100%全额退款保证
易品期刊网的成功录用率在业内一直遥遥领先,对于核心期刊的审稿严格,若未能发表,全额退款! 查看退款证明
- 上一篇:让幼儿园管理更精彩
- 下一篇:论‘精神的底子’语文化(二)

- 推荐
- 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