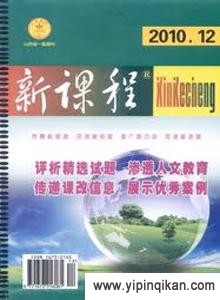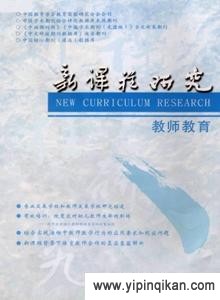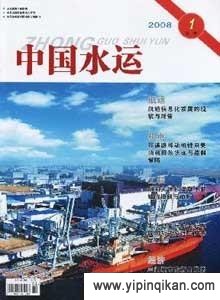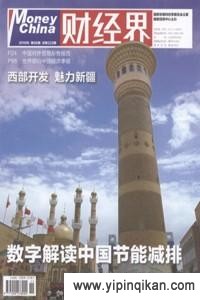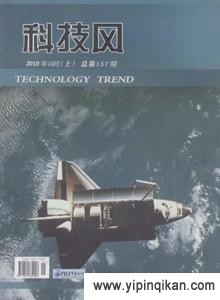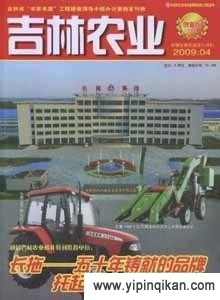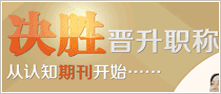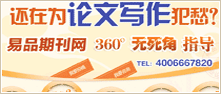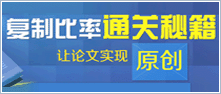中国民法典制定的三条路线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经历了“三起三落”,分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民法典的制定再一次被提上日程。第四次民法典的制定,最初遵循“三步走”的计划;2002年在领导人的推动下,一部“卤菜拼盘”式的民法典草案被提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讨论;在学界对2002年民法典草案的普遍反对之下,2004年,民法典的制定由“批发”改为“零售”,形成了先制定物权法,再制定侵权法、人格权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民法典的立法步骤。第四次民法典的制定,经历了“三条思路”的论战、要制定“物权法”还是“财产法”的争论、“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的争议等一系列的波折。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形成了“新现实主义”、“新理想主义”和“延期派”三条路线。民法的法典化,受到学术积累和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乃至民族情感等因素的制约,中国需要在这些条件成就的基础上,自然地、渐进地衍生出一部优秀的民法典。
【关键词】“三起三落”;新现实主义;新理想主义;延期派
【英文摘要】The enactment of Civil Code of the P. R. China has undergone three rises and three falls,which happened in the 1950s,1960s and 1980s respectively. In 1997,aft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ruling of the law and of safeguarding the human rights in the 31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enactment of Civil Code was put on the agenda again. Originally the fourth enactment of Civil Code was to be accomplished via the three-step strategy. But in 2002,due to the leader’s anxiety for success,a welter of Civil Code Draft was submitted to the 11th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inth NPC for discussion. The Chinese academia fighted fiercely against the 2002 Draft,therefore the route for the enactment of the Civil Code was changed from“wholesale” to“retails”。NPC decided to enact the Property Law first,then the Torts Law, Personal Rights Law and the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and eventually make up Civil Code on the basis of these laws. The fourth enactment of Civil Code endures a number of twists and turns,such as the debate over the three routes to drafting the Civil Code,whether to enact a Property Law or a Real Property Law, and whether the Property Law Draft is unconstitutional. Till now,there are three routes to enacting the Civil Code,the new realism route,the idealism route and the postponement route. The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 is subject to the academic background,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 environments,and even the national sentiment,hence an excellent Civil Code can evolve naturally and gradually only, if these conditions allow.
【英文关键词】The Three Rises and Falls;New Realism;New Idealism;Postponement Route
今天在台湾跟大家讲的这个话题,可能距大家生活比较远,但是,对于中国内地来说,离生活很近。因为民法是私人生活的法律,可能你一辈子碰不到刑法问题,但是会碰到民法问题。中国内地民法牵涉十几亿人口,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3亿多,那么,这一部民法典,就关系到世界上13亿多人口的生活问题。所以,中国内地民法既是老百姓关心的话题,也是海内外学者所关注的话题。
我今天跟大家从几个角度来谈我们民法的变迁问题。民法典在制定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波折,第四次民法典编纂刚开始时有三条思路。现在,基本形成了三条“路线”。我在考虑到底是用“路线”还是“路径”。因为“路线”好像意味着已经形成了一个指导思想,你就想这么做。打个比方,我认准了这个男孩子,我就要跟他谈恋爱,那是你的“路线”,是指导思想;但是,“路径”是说你慢慢地去找,谁合适,跟谁谈恋爱。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可能叫“路径”更适合,因为它不是既定了的,而是在慢慢形成当中的。当然,当前的这几条路径,几乎是先入为主地一下子形成了三种主张:汇编式的主张、体系化的主张、延期派的主张。这里,将分析这些主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宏观描述,基本上反应了中国内地目前的民法典的立法状况。
一、民法典制定中的“三起三落”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1949年之前,中国内地所适用的民法就是台湾现在适用的民法,即1929年开始在中华民国时期制定的民法。这部法典,1949年之后在中国内地被废止,但仍在台湾实施。中国内地废止之后,对民法典也进行过一些制定工作,基本上可以描述为“三起三落”。1954年制定了宪法之后,全国人大开始着手制定民法典。当时制定民法典,吸收了苏联的,当然也吸收了德国、日本的民法典,甚至包括美国的法律规定,但主要是苏联1922年的民法。这部法律还不错,沿用了一些既有的概念,包括总则、所有权、债法总则和债法分则,共分四编。[1]加上之前的婚姻法[2]和后来的继承法[3],类似德国五编制的改编。事实上,它也类似民国时期民法典的编制。但是,1957年中国内地发生了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即“反右”。“反右”的政治运动就是要清除掉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并让他们去劳动改造。当时中国内地一个比较有声望的学者谢怀栻教授(从战败的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台湾法院的工作,作出了中华民国接收台湾法院后的第一份判决书)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进了新疆的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民法典的制定工作,那时就中止了。这是第一次民法典的起草。
第二次从1962年开始到1964年结束。1962年毛泽东发出指示,针对国民经济中调整改善的问题,提出“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于是,民法典编纂工作再次启动。但很快,到了1964年,“破四旧”运动开始了。因为在1957年“反右”运动过程中,我们的政权觉得仅仅清理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够的,还有封建的糟粕,如旧的庙宇属于“旧的文化”,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等都需要被肃清。这样,第二次民法典编纂活动也中止了。
第三次民法典编纂大家可能知道一些。1978年之后,邓小平主政中国内地,开始施行一些开明的政治政策,1979年,也开始考虑制定民法典。邓小平谈到,“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我们的民法还没有,要制定”。[4]很快,1980年8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民法起草小组就出台了一个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至1982年5月1日,陆续出台了四个征求意见稿草案文本。[5]不过,此后立法方针改变了。因为制定一部民法典的任务太繁重,但是,当时中国内地社会急剧转型,迫切需要一些法律。比如说,此前中国内地是锁国政策,一旦对外开放的话,就需要引进外资,那外国人在这里投资就担心了:我来中国内地投资,共产党政策一旦变化,又来一个资本主义改造,把我的钱收走了怎么办?我在中国内地挣的钱能不能带走?有没有法律保障?于是,亟待制定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之类的一些法律。此类解决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等问题的法律,若等到民法典制定之后再行研制,那就晚了。这项工作,是由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主持的,他也是法制委员会的主任。他说,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目前难度比较大,我们可以先从制定其他的民事单行法开始。逐渐地,像《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等开始制定。后来,又说民事领域需要一个总的东西,于是就提出制定《民法通则》。整个工作,最后的结果就是1986年的《民法通则》出台。当然,其间还有一场是制定民法典还是制定经济法典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反映了中国内地“经济法学派”和“民法学派”之争。这一点,王文杰教授进行过深入的研究。[6]总之,《民法通则》制定之后,形成了内地的“民法通则+单行法”的立法模式。这样,加之《婚姻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收养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单行法,这种“民法通则+单行法”的模式,一直持续到1997年。
二、第四次民法典的制定过程
1997年,中国内地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变化,提出要“依法治国”,同时提出要保障人权。这一点,在中国内地历史上是很重要的。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把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作为目标。随之而来的,对立法体系的要求就是到2010年要在中国内地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这样一个目标模式之下,全国人大开始着手制定民法典。当时,参与制定民法典的有九位学者:王家福教授,曾经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所长;江平教授,曾经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魏振瀛教授,担任过北大法学院的院长;王保树教授,当时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副所长,后改任清华法学院院长;梁慧星教授,也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王利明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还有费宗祎、肖峋两位最高人民法院的退休法官;魏耀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的前任主任。这九个人,组成了一个民法起草小组,当时有一些分工。按照起草小组的设想,计划分“三步走”:1999年制定统一的合同法;之后用四五年的时间,完成物权法;再之后,形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1999年才会有《合同法》?其实,1999年之前,在中国内地是三个合同法并存:一个是《技术合同法》,一个是《涉外经济合同法》,一个是《经济合同法》。为什么会有单独的《技术合同法》?这反映了中国内地渐进式改革的实际状况。比如中国内地改革的时候需要引进外资,引进外资的时候自然希望先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过来,那么有关技术领域里的契约或合同就应该先有一些法律规范。同时,要对外交往,引进外资,也就需要制定一些涉外经济合同方面的规范。于是,根据市场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逐渐地制定了这些单行的法律。1999年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三部法律整编在一块儿。整编在一块儿的时候,有一些矛盾,有一些摩擦,当然也存在一些观念的转变。比如,制定《技术合同法》时据说是希望先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然后再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你引进的时候,别人不一定给你最先进的,因为国外企业的战略目标往往是不给你最先进的技术,比如美国对中国一直采取技术封锁,包括对台湾。它的大企业、大公司要技术更新,它肯定不给你更新了的新技术,而是把逐渐要淘汰的、即将要淘汰的技术先转让给你,然后再获取利益。你在它原有的旧技术之下生产产品,在此之后它马上更新它的产品和技术。所以,你一厢情愿地去引进一个先进技术是不可能的,人家不一定非要按照你的这个想法。这一轮的技术引进过程当中,我们有些地方要检讨。另外,我们发现,在技术合同、涉外合同和一般经济合同交往中,合同交往的规则是相通的。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要把合同法统一的想法。这个统一,当然也遭到一些抵制,因为在中国内地,《技术合同法》是由科技部的一个执行部门执行的,如果《技术合同法》寄生于科技部的话,科技部就有自己的一套行政人马,有编制、有经费来执行技术合同。如果三部合同法合并到一块儿,科技部的那帮人就要解散。这些利益上的区隔引起了一些争议,但通过一年的时间,合同法终于统一了。
合同法在1999年3月通过之后,按说应该花四五年的时间制定物权法,实际上,截至2001年之前,学者们也都在紧锣密鼓地做这件事情。特别是中国社科院的梁慧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由他们各自带头,分别有一个学者建议稿。[7]但是,到了2002年的年初,立法机构的节奏突变,要求当年年内就提交民法草案。这里有一个背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李鹏。李鹏委员长以前做过总理,学的专业是动力、水电,不是像大家一样学法律。他最初进人全国人大听取法律委员汇报时,王家福委员曾提出过,希望九届全国人大能够制定民法典。[8]李鹏委员长那时可能还不知道民法对社会生活有多么重要。后来,一些学者慢慢地跟他解释民法的重要性,并介绍说,拿破仑主持制定的民法典,当时叫《法兰西人的民法典》,但因为是拿破仑主持和指导的,最后为了纪念他,叫做《拿破仑法典》。这样,后期的时候,李鹏委员长意识到这个问题。按照任期规定,2003年3月,他就要离任。当年年初(2002年2月22日)的时候,李鹏委员长跟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说要起草民法典,把物权法的内容也包括进去,争取在他的任内,把民法典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一审,那位副委员长也同意。[9]其实,正如有的人大委员后来在审议民法草案时说的,“这么大的一个基本法跨届审议,会有一些不太好办的事情,建议先审议物权法,然后再审议其他3个新的法律,最后审议制定全面的民法。”[10]我曾经撰文对此进行分析,认为要制定一部优秀的民法典,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面临着许多的挑战。[11]一年的时间制定民法典,是在开玩笑。一个国家制定一部成功的民法典,基本上需要20年的时间。他当时要求2002年12月提交民法典草案,法工委肯定是按照领导的意见办。[12]这样,在2002年年初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召集学者开会说:你们不要再争论了,现在领导说要干这个事,并且要年内提交正式的法案,按照节奏,你们至少要在九十月之后把所有的稿子弄出来。于是,有些争议也就不争了。
此前有些争议,比如,中国社科院的梁慧星教授说要制定物权法,另一位中国社科院研究知识产权的郑成思教授说不能制定物权法,他说: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了,物权有那么重要吗?有形物赶不上无体物啊,比尔·盖茨的微软、可口可乐的商标,价值远远超过几栋房子。房子没有了、烧了,没有关系,只要品牌在,再建个工厂马上就起来了。所以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应该制定一个包括有体财产与无体财产的财产法,而不是物权法。[13]后来法工委说,你郑成思教授不是要搞知识产权的吗,你梁慧星教授不是要搞物权法吗,那你们各自起草一个相应的文本,然后我们法工委再考虑,先不讨论、不争论,现在要尽快地把东西提交出来。这样,导致了2002年的12月,也就是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把民法典草案仓促地拿了出来。这个法案,就是一个汇编式的民法典草案。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它形容成“卤菜拼盘”。[14]大家也肯定知道“卤菜拼盘”:这里是“口条”(猪舌),那里是黄瓜,这里是鸡蛋。民法典草案就是一碟冷盘,相互没有关联。这个草案,共分九编。第一编以民法通则为基础形成总则编;第二编是物权法编;第三编是合同法编;第四编是人格权法编;第五编至第八编分别是婚姻、收养、继承和侵权责任编;第九编是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这个民法典草案公布之后,学界一片哗然。在中国内地立法中,立法机构提上议事日程之后,按照全国人大的常规,三审通过,即一个法案提交全国人大,三读之后就会通过。这个草案提交上去之后,有些学者开始说,这个是新中国以来民事法律最大的成就,然后开始唱一些赞歌,其中包括很有名的学者。我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工作,有一天跟梁慧星老师聊天,梁慧星老师是社科院参与民法典起草的人员。我说,这样不行啊,如果官方的汇编式草案一出来,再有一些学者唱赞歌,人大的那些委员又不太懂法—我们全国人大有一个特点,很多人大代表是荣誉性的,很多代表都是非专业性的人士,无法进行这种识别。这个时候,如果专家还唱点赞歌,代表们一拍手,这个民法典草案说不定就通过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梁慧星老师聊,说这个事情不行啊,我们要发出另外的声音,我们要发文章,我们要谈观点。梁慧星教授说,是啊,好!这样,我在《法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这是一个“卤菜拼盘”式的民法典,需要批判。[15]另外,我与梁慧星教授进行了一个访谈,要梁慧星老师解释说之所以会产生汇编式民法典,谈谈他参与民法典草案工作的体会,并把这次访谈的内容公开发表。[16]当时,梁慧星老师说得比较尖锐,他解释说之所以会产生汇编式的民法典,是因为汇编式的草案当中,很多如婚姻法、合同法、收养法、继承法等编,都是现成的。这些现成的法律,是主持这项工作的顾昂然同志[17]以前在的时候制定的,如果这些法律被汇编进去,最后追索民法典的时候,就能追索到他。他不希望他的成果一夜之间没有了,所以说他们要搞汇编制。他们的汇编制,又得到了像江平教授这样“松散式”民法典思路的专家的支持。梁慧星教授说他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他们不就是想在民法典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嘛!梁慧星教授后来用他自己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即所谓“三不”政策,其中有一条即今后不再参加民法典的立法工作。梁慧星教授说,当时他们10月的时候把稿子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工委却将学者们的稿子放一边,还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汇编思路来。梁慧星教授说,那要我们干吗?又没有给钱我们,义务劳动,劳动了之后还把我们不当回事儿,表示今后不再参与立法工作了。这样,民法典草案起草小组就算解体了。不过,梁慧星教授、徐国栋教授和王利明教授等学者主持下的民法典建议稿,还是先后出版问世,体现出了学者们的各种民法典理想。[18]
梁慧星教授所说的2002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讨论和决策,在李鹏委员长(2002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曾记载如下:“上午10时左右,在大会堂河北厅召集人大法工委的几位同志,包括顾昂然、胡康生、王胜明,还有何椿霖同志,开了一个关于起草民法典的座谈会。经过大家反复研究认为,现在起草的这部民法草案是基础,讨论了民法典编纂中的重要原则,不代替单行法。在民法典中应该既有物权法的内容,也有单行的物权法。这样做,便于充实和补充民法典内容,也可以避开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留有立法空间。民法草案争取在12月上常委会。”[19]不过,在12月29日常委会一审之后所引发的争议,则是这次座谈会上的人所始料未及的。学术界议论官方拟定的民法典草案之后,全国人大有点为难了。因为按照立法的节奏,法律案一般三读通过,人大已经一读了,下面两读之后就要通过,但学界议论太多。好在当时一读审议的是李鹏任委员长的九届全国人大,紧接着第二年(2003年)的3月全国人大换届,吴邦国接任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新的一届全国人大,先搁置了一下民法典草案。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时法工委民法室巡视员河山说:“用这种方式编撰民法典,全世界独一份,法律界称道的甚少,几乎没有听到说好的。” [20]当时,我把梁慧星教授的访谈发表在我主编的出版物《私法》上,寄给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就说,你们学者都说民法典草案不好,怎么办呢?草案已经“上马”,即进人立法程序了。草案一审是2002年年底的事情,2003年基本上搁置了一年。但是,搁置也存在问题。一个立法草案不能老搁置在那里,正式的立法程序已经启动了,应当往前走。跟高铁一样,高铁很快,坐上去了就得动,不能老在这里呆着。因为按照运行程序,你说了什么时候要开车的!这个事情,后来就由“批发改零售”了。全国人大说,完整地审议一个民法典草案比较困难,现在我们由“批发”改为“零售”,现有的就是物权法没有,侵权责任法没有,人格权法没有,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也还没有。这样,我们就先搞“零售”。“零售”的重点就是物权法,然后再制定侵权责任法。这个模式,似乎是回到了原来“三步走”的立法思路,不过是一个修改了的“三步走”节奏—将“三步”(合同法→物权法→民法典)扩大至单行法“多步”(如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等),然后修改《民法通则》为总则编,以此形成民法典。
“批发”改“零售”之后,首先是制定物权法。2004年8月,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出了一个修改稿,10月的时候拿过来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了之后,当时的计划是在2005年7月向全国征求意见:吸纳意见之后,计划在2006年3月通过。但是,在2005年征求意见的时候,出现了一点波折。北京大学的巩献田教授在网上发表文章,说物权法草案违宪。[21]我那时在美国,民法界刚开始对他的声音没太在意,因为他以前是南斯拉夫的博士。大家可能对南斯拉夫不太了解,但是大概知道它的意识形态。巩献田教授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宪法里说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这话听起来好像是说,公有财产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个人财产只有合法的才受保护。在语调上,二者似有些区别。这些语调区别,没有体现在物权法上,物权法也应该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在一体保护,不就是违宪了吗?!而且,他的调子更多地体现在物权法保护了富人的财产。平等地保护富人的财产,平等地保护像郭台铭先生的财富,和平等地保护乞丐的一个饭盆,那能叫平等么?那不叫平等,那实际上承认了社会差别。他当时提出了很多按照我们现在分析是极“左”的东西、计划时代的东西。民法学界当时没重视,觉得他的言论不可信,没什么影响力。我2006年春节回国,和民法学界学者聊起来,学者们说现在他(巩献田)影响大了,我们立法的决策都变了,要我赶紧写文章。我后来写了一篇连注释一起差不多10万字的文章,给学者和法工委的同志看,是批判巩献田教授的。[22]巩献田教授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所谓的“神圣”是应该被供奉的,和民间交往没关系。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有些问题。但是,那时他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与当时中国内地的场景相关,因为中国内地当时贫富差距很大—现在也是。由于贫富差距,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大家反思,市场导向的改革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要重回到讲求民生、均贫富或者说纯粹的计划时代?当时有这样一种呼声。特别是以“违宪”的帽子打下来以后,没有哪一个政治人物敢动这根底线。我不知道在台湾怎么样,但是我想在美国和中国内地是一样的,政治人物求稳怕乱,只要涉及“帽子”或“敏感政治”的问题,宁愿不沾边,宁愿缓下来,避免政治风险。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还把巩献田教授请过去,问他到底有什么想法。谈到最后,法工委同志说,巩献田你是在否定改革嘛。巩献田教授就说,他就是要否定改革,他觉得改革是有问题的,说你们现在的搞法和毛泽东时代的不一样;毛泽东时代多好啊,计划时代。这样,“左”派的争议很大。那时经济学界有一个“郎咸平现象”,有一个香港的经济学家到中国内地去,煽惑领导人,煽惑媒体。应该说,曾一度,“左”派占了上风。2005年年底,受此影响之后,当时有一些激进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在北京的西山开了一个会,后来把它叫做“新西山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些学者说了些很不好听的话,因为这个会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高尚全主持的,最终的格调是要继续深化改革,并且要承认改革,呼吁领导人要出来讲话,不能老站在后面,这样对社会思潮会有些负面影响。最后,在2006年“两会”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高调出场,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支持物权法。由于物权法是一个基本法,需要全会通过,2006年不能通过之后,于2007年通过了。2007年审议并通过的时候,也做过工作。2007年审议物权法草案的时候,像巩献田教授等一些人,曾经给全国人大代表发短信,想说服他们不能投票赞成物权法通过,说物权法是个违宪的东西,不能让它通过。最后领导做工作,说物权法要通过;物权法不通过,就证明我们对非公有财产不能和公有财产平等地一体保护。你不能平等保护,你就无法发展生产,无法形成成熟的市场机制。财产如果不能得到平等的保护,那是有问题的。后来,物权法就在这种政治的压力之下,高票通过了。2007年物权法通过后,紧接着,应该制定侵权责任法了。
物权法通过之后,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有一个调整,先进行了《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23],大概在2007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侵权责任法立法研讨会。在那个会议上,启动了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启动的时候,我们不太乐观,认为侵权问题涉及生活的范围很广,它不可能一下就通过。《物权法》既然折腾那么久,中间有反复,《侵权责任法》也应该是一样的。侵权涉及医疗损害,涉及机动车责任到底怎么分配,保险怎么介入等问题。前两天,我参加台湾举办的实证法研讨会。[24]其中,医学界的人说到“医闹”现象,即出现医疗事故后找医院闹事的情况。“医闹”现象在台湾也存在。在中国内地,“医闹”现象也非常盛行。在这种情况之下,《侵权责任法》的通过,估计也是很困难的。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对侵权法研究最成熟的是在美国。美国比欧洲成熟,就是因为美国比较重视个人的责任。欧洲注重社会保障,注重保险,侵权相对不发达。美国社会相对讲求竞争,同时也有一些社会责任,这样的话,美国的侵权法律制度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侵权法不是很好学习,不像大陆法,拿到德国的或者日本的文本,就可以学习。美国的侵权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判例法,大量的判例散见在侵权法中。但事实上,《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过程一帆风顺,就是因为学者没有兴趣了:立法嘛,折腾一下,应付一下算了。以前,大家对围绕民法典的立法都具有很高的期待;后来,没有太高的期待了。本来,预计《侵权责任法》会在2010年3月通过,但在2009年12月26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被提前”通过了。为什么要在这时通过呢?当时,全国人大在征求意见之后进行了考虑:《侵权责任法》很有可能在2010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通不过。因为面对这些众多的人大代表们,不好做工作。并且,《侵权责任法》不像《物权法》,《物权法》是对财产一体保护,涉及社会制度,领导层可以做工作,让大家思想开明一些。但《侵权责任法》不一样,到底是医院的责任要加大还是患者的责任要加大,如何举证,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保险如何介人,这些问题不好做工作,它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又要考虑到2010年中国大陆民事法律体系的完善,法工委的同志向人大常委会做工作。人大常委会的人少一点,人大代表们的人数却很多,所以《侵权责任法》就在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了。人大常委会通过《侵权责任法》之后,有的人说这违背《立法法》,因为《侵权责任法》也是基本法,它应该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会上通过,而不应该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不管怎样,现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都通过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按照原有的计划,有一个《人格权法》。但有可能,《人格权法》最终就不再单独制定了。原来极力主张制定《人格权法》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现在,又多了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立新教授,他还整了一个专门的《人格权法(草案)》专家建议稿。[25]但是全国人大民法草案出来之后,那《人格权法编》30多条没有太多的价值。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王利明老师民法草案建议稿出来之后,我跟谢怀栻教授聊过一次。这30多条,实际上可以合并成10多条;这10多条也是宣示性的,宣示有什么样的人格权,比如隐私权、名誉权、姓名权,只是在宣示。人格权不像财产权,财产权不仅是要宣示,更多的是要利用。比如你对某物享有所有权,那么别人可以去用益它,也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使用,也可以去耕作,或者说也可以拿到银行去担保。物权中,利用占了很大的部分。但大家对人格权有一个基本理念,人格权是不能被利用的。即便是在利用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那是商业化的利用、商品化的问题,那是后续的问题。在民法典当中,我们还一时很难考虑大量的利用性质的问题,至少时代尚未发展到那一种状态。而如果仅仅为宣示性的规定,就没有必要单独作为一编,可以放在总则,或者在侵权法中宣示一下,甚或分解在个编,就算可以了。所以,《人格权法》可能是不会制定了。[26]剩下的,就是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那是冲突规范的问题。[27]总则的问题,与《民法通则》相关,直接修改一下。
三、民法典制定的“三条路线”
什么叫“三条思路”呢?其实,它也是在民法典制定过程当中形成的。2001年的时候,9位制定民法典的专家,同时也有全国的其他学者参与,形成了这几条思路。一个就是“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认为中国处于转型的过程当中,不可能做一个全面的立法。美国人没有民法典,也挺好的;美国的判例法加上商事成文法,再加上美国法律协会(American Law Institution,简称ALI)做的法律整编(restatement),这种联邦式的、松散式的立法也挺好的。中国内地的这种松散式的立法也不错,单行立法,社会一变化,马上修改单行法。如果一个民法典放在这儿,要修改起来可麻烦了,很不适应急剧变动的社会发展。法典一旦颁布出来,它往往就落后于时代了。这个时候很不便修改,你还不如就采用单行法。这是江平教授、费宗祎法官、魏耀荣主任主张的一种模式。[28]这个模式出来之后,最早并没有人重视,大家都认为这不是一个民法典的模式,它是一种不要民法典的模式。第二条思路就是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思路,这是德国法的思路。他认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思路。第三条思路就是徐国栋教授的“理想主义”思路。这是梁慧星教授归纳的“三条思路”。[29]
徐国栋教授任教于厦门大学,梁慧星教授的关于三条思路的文章出来之后,立刻遭到了徐国栋教授的反唇相讥。徐国栋教授说,他的思路是“新人文主义”的,不是“理想主义”的。[30]现在谈“理想”,大家觉得很幼稚。不知道你们现在是怎么样的,说你这个人好有理想,好像就是说你这个人好幼稚啊。在中国内地,好像就是这样。徐国栋被认为“有理想”之后,立刻觉得自己“被幼稚”了。在他“被幼稚”之后,他立刻反唇相讥,说他是“新人文主义”,梁老师的是“物文主义”。这样,就引起了口水之争。我为什么把它叫“口水之争”呢?因为争论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看徐国栋教授的“新人文主义”的方案。他要制定两编,一个是人身关系法,另外一个是财产关系法。两编之后,有分编。有自然人、法人、亲属、继承,它是以人身权为基础的;然后,就是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物权、智慧财产权、债法总论、债法各论。他是这样区别。事实上,他的两编,是指人和物的两分法。他所谓的“人文”,是指把人身权放在财产权的前面,这个不构成理由。因为民法典有总则的时候,总则也会把人的问题放在前面。任何一个立法,首先都会介绍什么样的一个人干什么事,这样。自然人、法人就都放进来了。只不过,德国法处理的方式是放在总则里。他的争执实际上是八编制。而且,这种八编制的划分是有交叉的,我们很难说继承法就是亲属关系法。你作为女儿的身份已经固定了,但是你继承的是财产,也可能是债务,这个是财产关系,很难把它完全界定为身份关系。相应地,智慧财产中的署名权等,都是人身权,人身权的部分,你把它放在财产关系法里面,更不妥当。所以说,徐国栋教授所谓的“人文主义”方案,是他自己制造的一个噱头,标新立异。这个里面,有些口水的味道。由此,他与梁慧星教授交恶。梁慧星教授是徐国栋教授在中国社科院导师组的老师,两人也断交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被忽略的争论还有一些。比如说物权法与财产法的争论,这是郑成思老师与梁慧星老师的争论。这个争论,前面提到过。在这种情况下,郑成思教授和他指导的两位博士,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内刊—这个内刊是给领导人看的,把他的想法写成三篇文章,在《要报》上发表了。文章放在《要报》上之后,梁慧星教授很反感,说要就搞学术争论,怎么放在《要报》上面给领导看,要领导压我们。于是,梁慧星教授也要把自己的观点放在《要报》上,他去找《要报》发表他的文章,《要报》不发,他很愤怒,然后就发表在网络上。当然,两位先生的争论,都在《私法》上公开发表了。[31]同时,这些争议,在网络上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后来,中央领导决定要尽快制定民法典,法工委就出面制止争论,要他们别争了。法工委同志说,你梁慧星不是要搞物权吗,你郑成思不是要搞知识产权吗,那你郑成思搞知识产权法编,他梁慧星就搞物权法编,你们各自提交自己的东西。不过,在提交的过程当中,知识产权法编由郑成思教授主导,后来把吴汉东教授拉进来,制定一个知识产权法编。[32]最后,知识产权法编在2002年九十月的时候被放弃了。为什么呢?知识产权在台湾称为“智慧财产”,智慧财产领域本身有很多单行立法,其中有很多的程序性的规范和行政性的规范,比如说专利无效的申请,告智慧财产局是作为行政诉讼,是行政法院受理的序列。台湾在2008年成立了“智慧财产法院”,但是“智慧财产法院”上位的法院之一,也是分属于行政高等法院,它涉及程序,涉及行政。怎么样融合到里面去,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仓促之间,知识产权法编很难做,因为这样一个命题—怎样去整合智慧财产或知识产权,是市民法必须面对的。我们的民法典是市民法典,是私人法典;既然是私人法典,就要包括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在的东西,几乎都和知识产权相关:我们坐的椅子可能涉及外观设计,你拿的书涉及版权,同学们的手机可能有很多的专利技术。所以,我们生活和知识产权密切相关,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但是,它应该怎样被整合到传统的民法典体系当中?其实,这是近10多年甚至20年来西方财产权理论界想去整合的问题,比如说知识产权哲学,把知识产权的合理性与传统财产的合理性放在一块儿来讨论。在财产权的框架之内,如何整合智慧财产等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
另外,巩献田教授的争论显现了一个观念,就是私权观念如何再生。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在中国内地这个社会,还有一些计划思想在里面。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一个私权观念再生的问题。私权观念再生很重要,我们过去都是自己做主,所谓“我的事情我做主”!我跟人家签合同,由我做主;现在你会发现,你做不了主,你去签合同都是格式合同,买东西都是格式条款。这种情况下,私权观念怎么再生?同时,法律如何去照顾被社会挤压、在社会生产线机械运作的那些人的生活,即在社会化运动中个人如何重获自我,这是民法典所面临的艰巨的问题。巩献田教授实际上提出了这两方面—中国问题(计划思想)及中国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私权观念再生),涉及中国民法典的成长问题。
当然,总的来说,2002年12月民法典草案改变了这一切。过去梁慧星教授归纳的“三条思路”,现在完全变化了。梁慧星教授后来说了,像这样的民法典,他宁愿不要。徐国栋教授也失语了,他也不谈他的人文主义了。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明教授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倒是真正和全国人大立法规划跟得很近,推动了很多(立法工作)。其实,在现实主义思路中,在梁慧星教授和王利明教授之间,王利明教授更加趋于现实主义合作路线。比如说,梁慧星教授在解决物权问题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把台湾的某些制度移植过来。台湾“民法”以前的永佃权后来改为耕作权,现在改为农用权,他更多的是把这些移植过来。而王利明教授则是在中国内地的“承包经营”的基础之上,改为农村承包经营权,这与中国内地的这种概念文化更契合。所以说,王利明教授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路线,他对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做了很多努力。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尚不成熟。1804年的时候,拿破仑制定了一部法典,名垂青史。18至19世纪之交的这部民法典,影响了200多年。同样,也是在19至20世纪的世纪之交,德国民法典也承载了整个大陆法的法律文化以及成就。中国内地现在制定民法典,也处于世纪之交。我们的学者、立法者都说,我们要创造新世纪的辉煌,我们要制定最优秀的民法典,代表21世纪最新成就。。当时,我就在唱反调,但人微言轻。我说,民法法典化是受到限制的,它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不是想制定就能制定的。而且,即便是有政治人物推动,但不是你想推动就能推得了的。很多民法典,都是由政治人物推动的,像法国的拿破仑;德国民法典也是被一定的政治需要推动的,比如统一德国。中国内地这个民法典草案出来之后,大家看到,果不其然,条件不具备,很难制定一部很好的民法典,就是像物权法,这样的根本性问题都不能解决。[33]
我的这个观点,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定的认同。其实,下一步如何走,人大法工委现在也在思考。通过我的观察,逐渐地形成了三条“路线”。我前面提到,也有可能是“路径”,因为它不是一定要这么走的。第一条,新现实主义路线。如果借用过去说法的话,就是以汇编模式为基础的改革办法的实用路线。全国人大法工委现在所做的,就是以改革办法为基础的实用路线。当然,这一条路线到底是沿着改革开放初期确立的“《民法通则》+单行法”模式,还是由“三步到位”(“三步走”规划)改“多步走”模式,似乎还不明朗。如果以2010年确立社会主义民法体系而论,事实上就是改革初期确立的改革办法模式。这样一种“新现实主义路线”,比较实用,当然也会有一些弊端。应该说,这是一条“走老路”的新现实主义路线。第二条,就是新理想主义路线。新理想主义路线仍然是个理想主义的模式:完整的逻辑体系,体系化的内在要求,像德国民法典那样。第三条路线,是前面提到的延期派的主张。我的观点就是第三条路线。这个民法典不要去强求它。你在改革中发展,等到历史文化、学术积累到一定程度,民法典自然会到来。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像美国法律协会那么做,做一个中国民事法律的整编工作。因为中国内地的民法非常粗糙,很原则性,要把民事规则、习惯、司法判决的一些成就,把各种行政方面的相关规范,进行理论性地整合,整合之后,逐渐形成更详细的具体规范。简单地说,就是发现民法,即整编或重述民法。这个工作做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条件允许了,再去制定一个民法典,是可以的。所以,虽然领导强力推动物权法,通过了,但物权法里有很多的政治性的腔调,如“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物权法》第3条)用语,这不叫物权法,这是宪法。所以说,我主张一种自然衍生的路线。现在的积累,就是在自然衍生,是一种渐进路线。这种渐进路线,是一种因应我们法治建设的模式。我所主张的是延期派,主要路线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采取“民法通则+单行法”的模式继续;同时,进行法律整编工作;条件时机成熟的时候,民法典会自然衍生。这也是一条不放弃理想、但却尊重现实的道路。大家谈恋爱也要这样,不要预设男朋友或女朋友要多高的,多苗条的,应该慢慢交往。因为你的理想、你的前置条件可能是错的,因为你现在还不成熟。你会在生活中去慢慢地磨合,你会发现怎么样是最好的。你会有理想,你还是会想找一个很好的女朋友或男朋友,但是你还是要不断地去发展。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制约民法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学术传统及学术水平的发展程度。法典化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学术法的发展。学术积淀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学术法发展之后,再慢慢过渡到法典化。这是法典化的规律,是学术传统及其发展程度决定的。另外一个(第二个因素),公权力对它的容忍、干预程度。公权力的干预程度很深,民法的发展会受到影响。第三个是经济因素,即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现在经济因素比早期单向度地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情形要复杂得多。除了依然存在市场成熟度不够、总体不足之外,局部市场过渡、经济力强烈影响市场公平与自由竞争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市场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记载民法典中体现自己决定能力与社会化的两个维度,是未来民法典的一个深刻命题。第四个就是文化因素。民法文化是一个权利文化,权利文化需要建立起来。另外,还有些政治因素和民族情感因素。其实,民族情感因素在任何立法的时候,特别是大的立法时,都会存在。比如像罗马人,他们制定《十二表法》的时候,派人去古希腊学习梭伦立法的改革,然后制定出《十二表法》。这是一个向希腊学习的过程。罗马自己没有哲学家,但他们的法律为什么那么繁盛?罗马法吸收了希腊人的立法经验。但罗马人老不承认,总觉得这个荣光属于自己。德国也是一样。《拿破仑民法典》出来之后,很多德国人都说要制定民法典,有的甚至说先直接将法国民法典拿来;但有的德国人就说了,我们德国人那么注重思维,我们这么优秀的民族,怎么能把法国人的东西拿过来就用呢?!当时,德国人就说,把法国的法律拿过来用,有伤我们的民族感情,有伤我们的自尊心。我们要在他法国人的基础之上,制定更好的,结出更多的成果来。甚至,包括中华民国时期制定民法典,当时国民党政权都是很避讳的,日本当时在伪满洲国移植过它的民法典。伪满洲国民法典吸收了日本法的一些成就。因为日本民法典制定之后,它法学理论就更新了,但民法典不可能老改。于是,日本学者们就把一些新的成果放到伪满洲国民法典中去。但是,一说要吸收深受日本人影响的伪满洲国的民法典,蒋介石先生答应吗?咱们的故主席毛泽东先生会答应吗?都不会答应。所以说,它涉及民族感情。特别是像这种标志性的东西。总之,我们把它简单地归纳一下,一个国家要制定民法典,要适应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心理文化等,同时,也要能够应对时代的挑战,特别是大陆法系法典模式的挑战,以缓解现代法的危机。[34]
这是我第二次到政大来。前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教授在一块儿谈。后来,苏永钦教授跟我说,你知道了吧,我们这儿德国法的味道很浓!其实,不光是这里,台大也是如此。到了台大,都是德国派。现在,您如果有机会去德国,您会发现,连德国教授自己都承认,知识产权领域,肯定是美国人的;商事的、合同的、侵权的,基本上都是美国人的;国际贸易这一块更不用说。因为它的技术领先,它最先碰到问题,它最先拿出解决方案。而且,它的司法机制、判例法以及单行的成文立法模式,很能适应社会发展。它不需要有我们那么多条条框框。这就是英美法的好处。英美法能够发展到今天,携带着它强势的技术、强势的文化、强势的经济。你要跟美国交往,要么你就要用它的模式,要么你就不跟它做。合同、商事都是它主导,金融更不用说。所以,整个这一块,大陆法都面临着转型和融合的问题。
现代法在大陆法系传统模式中有一些危机。如何去面对这些危机?在中国内地也面临着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国内地的实践比台湾丰富很多,因为中国内地幅员辽阔,人口复杂,地区差异非常大。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会提供很多经验性的样本;这些样本,对学术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具体的挑战,实际上就是我谈过的整个财产权体系。另外,就是人格权扩张的类型化。人格权是不断扩张的,存在一个发现的过程,比如说像隐私,过去没人谈隐私,可能是美国的某个人的老婆经常被报社记者弄得生活不安宁,所以他们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论隐私权》。[35]结果,隐私权就获得尊重。权利是不断衍生的,如商品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生育权、受教育权等,这些以前大家都没有的概念,现在都慢慢地出现了。人格权也一样,它是不断扩展的。在扩张的过程中,如何形成一个一般条款并权利分类,这是面临的一个挑战。还有一个,私权观念的形成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再生。规制缓和和加强规制,是两大难题。一方面要加强规制;但是规制过多,人会受到压抑,大家都会跳楼。深圳富士康员工的“跳楼事件”截至目前已经9起了。就是说,规制太多之后,人会受压抑,社会也是如此。为什么那么紧张?需要缓和!规制缓和,就是自己做主,自己身心愉悦,这是民法追求的根本。这个时候,存在私权理念再生的问题。另外,民法典承载着促进社会进步、建构市民文化的功能。即使说没有民法典,但是民事立法、民事权利在社会当中的运行会形成一种文化,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孟德斯鸠考察后发现,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民事立法很兴盛,那么这个国家民主、文明的程度就高一些;反之,这个国家民主、文明的程度就要低一些。“所以当旅行家们向我们描述专制主义统治着的国家时,他们很少谈到民法。”[36]这是他考察以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们的民事制度,是否能够承载这些功能?我们具备了民法典制定的条件没有?如果以前没有,那么现在是否具备这个条件?事实上,它可以转换为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够因应这种时代的挑战?对于我们的民法典来说,它应该承载了很多人的期许。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只会找到中国内地这样一个生活丰富的经验样本。当然,你可以说我们去马尔代夫(The Republic of Maldives)搞一个试点,但很遗憾,马尔代夫是个岛国,200年之后很可能就没有了。大家可能不跟它做生意,因为它的影响力很有限,它要制定非常精美的民法典没有多大的意义,它不能影响到全世界,不能对我们社会生活发生太大的影响。而像传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瑞士、日本、德国、法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你要它去改变自己的传统,那是不可能的。法国民法典修修补补,到现在还屹立在那里,它觉得那是它的光荣,它引导了世界的革命、资产阶级权利运动,它吸收了17世纪以来的自然法典运动的成就。它承载了很多的光荣和光环,“法国人民对这部法典充满着爱好和感情”[37],它不可能被废弃掉。所以说,唯有我们这一块巨大的试验田,可能影响世界的巨大场域;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德国、日本、瑞士的学者,包括台湾地区的学者,对中国内地的立法很感兴趣。我们在做民事法律整编的时候,建立了中美民法小组、中欧民法小组,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海峡两岸民法工作小组。日本也正在和我们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学者们,像王文杰教授,总是希望把他的研究成果,传播给大家,对社会有用,他就感到很满足了。这是学者的一个偏好。很多学者都希望他的思想成就能够在这里体现,因为没有其他的试验场,只有在这里才能实验,才能找到成就感。学者在期许,当然老百姓也在期许。因为一旦民事生活走向市民社会的基本建构,那么,对于社会的长远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的制度,好在美国藏富于民。美国的民事权利的增长,不是通过民法典,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司法制度配合它的权利文化,它可能是更有效的。在中国制定民法典,也承载了我们这些期许和机遇,所以说,我们更加关注这样一个话题。
四、结语
也许,从“三条思路”到“三条路线”,我们的各种主张都是殊途同归。像我主张的延期派,并不排除今后自然衍生出一部民法典。甚至说,这是一种怀抱理想的务实(现实)选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采取的新实用主义路线,或许正在朝着民法典迈进。现在他们搞单行法,但最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进入成熟的常态社会,也有可能制定一部优秀的民法典。当然,有些学者的理想主义或者说过去的那些理想,注定是要衰落的了。单从官方立法取向来说,已经放弃了它们。从现有的民事立法模式及单行法的一些文本来说,很多学者的理想也已经失落了。而就一部成熟的民法典或者说能够代表21世纪最新成就的民法典来说,那些学者们各自心仪的自己主持的文本是否承载或反映了这些,这里我们不必去评说。诚然,挑战一个进步的时代,或者说反映一个时代的进步,对于一部市民法典的制定者来说,总是有些困难的。比如说荷兰民法典有知识产权编,俄罗斯民法典也有知识产权编,虽然知识产权编的框架也都出来了,但是具体的条文没有出来。无论如何,我们的一些学者建议文本,为后续的研究和立法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而且,也不排除那些学者们现有的这种思路或方案会不断地改进,会不断地革新。也许,从最终的结果来说,我们都是殊途同归的。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现实之中,我们的生活会趋于共同的走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无法超越这些现实—无论现实给予我们的是希望还是失望。
【注释】
[1]各编及其历次草案,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上卷、中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全文分8章27条,文字简洁,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兼及家庭关系,确立了现代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制度。
[3]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中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页以下。
[4]邓小平:《民法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载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5]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下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页以下。
[6]参见王文杰:《嬗变中之中国大陆法制》(第2版),新竹:台湾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以下。
[7]后来,这两份学者建议稿先后正式出版,分别参见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8]参见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731页。
[9]参见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734页。
[10]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746页。
[11]参见易继明:《民法典的不朽—兼论我国民法典制定面临的时代挑战》,《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
[12]参见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735页。
[13]后来,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在2002年12月25日分组审议民法草案时,郑成思教授也谈到,“整个物权称为财产权好一些。涉及有形物的叫物,其他物通称为财产”。参见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页。
[14]参见易继明:《认真对待学者—闲话学者与最近的民法草案》,《法学》2003年第5期。
[15]参见易继明:《认真对待学者—闲话学者与最近的民法草案》,《法学》2003年第5期。
[16]参见易继明:《学问的人生与人生的学问—访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3辑第2卷(总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17]顾昂然同志曾长期在全国人大工作,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资料室编译室主任、研究室主任、民法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93年至2003年,一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并在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期间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8]先后出版的三份代表性学者建议稿如下。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王利明:《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9]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735页。
[20]河山(何山):《物权法制定之焦点》,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5辑·第1卷(总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第29页。
[21]巩献田:《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为〈宪法〉第12条和86年〈民法通则〉第73条的废除写的公开信》,
[22]易继明:《物权法草案“违宪”了吗?—质疑巩献田教授的〈公开信〉》,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7辑·第1卷(总第13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23]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于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24]2010年5月19日至20日,台湾“第五届法学实证研究研讨会”在台湾交通大学举行,笔者应邀参加并作了主题发言。
[25]参见杨立新主编《中国人格权法立法报告》第4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以下。
[26]当然,在2010年10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据个别参与民事立法的学者介绍,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展开《人格权法》的立法工作此言论,不知是立法机关的真实意图,还是个别学者为了推动人格权单独立法所实行的“推动之举”。对此,笔者持审慎的态度。
[27]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已于2010年10月28日审议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该法于2011年4月1日起施行。
[28]参见江平:《制定一部开放型的民法典》,《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又参见江平:《再谈制定一部开放型的民法典》,《法学家》2003年第4期。
[29]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30]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大论战》,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83页。
[31]参见郑成思等:《是制定“物权法”还是制定“财产法”?》,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4辑·第1卷(总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又参见梁慧星:《是制定“物权法”还是制定“财产法”?—郑成思教授的建议引发的思考》,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2辑·第2卷(总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32]参见郑成思:《民法草案与知识产权篇的专家建议稿》,《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33]参见易继明:《民法法典化及其限制》,《中外法学》2002年第4期。
[34]参见易继明:《民法典的不朽—兼论我国民法典制定面临的时代挑战》,《中国法学》2004年第5期。
[35]See Samuel D. Warren, Louis D.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Harvard Law Review,Vol.Ⅳ,December 15,1890, No. 5., pp. 193-221.中译本参见[美]塞缪尔·D.沃伦,路易斯·D.布兰戴斯:《隐私权》,易继明译,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6辑第1卷(总第11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99页。
[3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4页。
[37]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1卷(总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 认准易品期刊网
1、最快当天审稿 最快30天出刊
易品期刊网合作杂志社多达400家,独家内部绿色通道帮您快速发表(部分刊物可加急)! 合作期刊列表
2、100%推荐正刊 职称评审保证可用
易品期刊网所推荐刊物均为正刊,绝不推荐假刊、增刊、副刊。刊物可用于职称评审! 如何鉴别真伪期刊?
都是国家承认、正规、合法、双刊号期刊,中国期刊网:http://www.cnki.net 可查询,并全文收录。
3、八年超过1万成功案例
易品期刊网站专业从事论文发表服务10年,超过1万的成功案例! 更多成功案例
4、发表不成功100%全额退款保证
易品期刊网的成功录用率在业内一直遥遥领先,对于核心期刊的审稿严格,若未能发表,全额退款! 查看退款证明

- 推荐
- 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