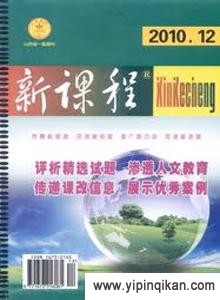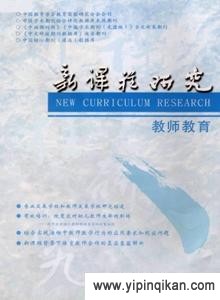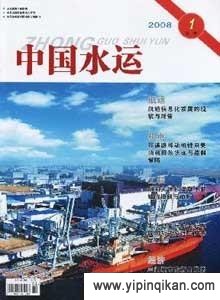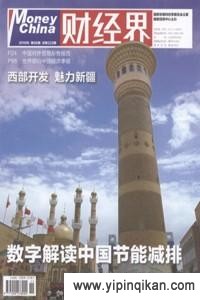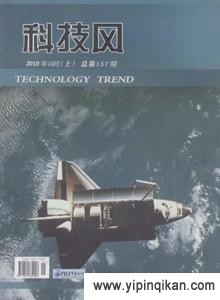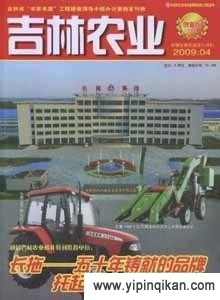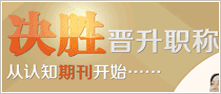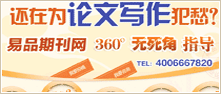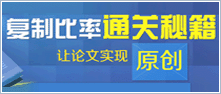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神圣性
时间:2010-12-08来源:易品期刊网 点击:
次
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神圣性
张世英
生活艺术化的深层内涵,不在于悦人耳目的声色之美,而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于心灵美。
本文结合海德格尔、布伯、李贽等思想家的相关论述,着重阐明心灵美之超越感性美的特点。
艺术品之美的本性,在于超越(不是抛弃)日常物品的功用性,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一次性的)世界。
“全新”之为全新,在于一反常态生活中功用性之“非功用性”。
这是一种不同于生活情态的审美情态。
生活艺术化、审美化,必然地、自然地蕴含着人的道德境界、精神素质的提高。
当前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低俗之风,损毁了艺术的神圣性,非真实的艺术和审美,也有违德育之旨意。
一、从美在声色到美在自由在“生活艺术化”的国际思潮的大背景下,人们热衷于“五色”、“五音”之美,热衷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美,应可视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之自然趋势,无可厚非。
问题在于,声色之美,或者说,感性美,是否就是美之极致,就是美的核心。
柏拉图《大希庇亚篇》中关于“美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①的定义,把美的特点只赋予视觉和听觉,此种声色之美遭到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批判。
但这个定义本身所蕴含的审美感官和非审美感官的区分,却显示了审美的兴趣不同于实际兴趣的独特之处,这是很有意义的:视觉和听觉的对象,不同于味觉和嗅觉的对象,后者涉及人的感性欲念和功利追求,而前者无功利欲念的牵挂。
“望梅”可以产生美感,但并不能满足“止渴”的功利欲念。
中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申述了美的这一定义的深层内涵,继承公元3世纪古希腊最后一个伟大思想家普罗提诺关于“美源于上帝”的基本思想,认为事物的对称之美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为神性的象征。
美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实物,在于超出欲念功用之上。
这一思想揭示、扩大和加深了“美在于声色”的含义,美由此而可以定义为超越功用欲念之意。
比起苏格拉底、柏拉图之重审美的效用性观点来,显然提高了审美的超功利的地位,尽管他并不很崇尚艺术品,认为艺术品是人造的,不及上帝所造的自然事物之美那样更能显现“真”。
康德继承和发展了阿奎那的思想,强调美是惟一独特的不计较欲念功用的愉悦之感,他称之为“自由”的感情,即不受欲念功用制约之意。
在康德看来,不计欲念功利———自由,乃艺术创造之精髓。
“美在声色”的思想和命题从此明确地发展为“美在自由”。
但康德认为,艺术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审美意象”,即理性观念的感性形象,这里所要显现的是具有最大普遍性的概念———“理想”,类似后来黑格尔所发展了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说中的“理念”。
所以康德的艺术创造的产物,仍然是柏拉图式的“理念”,属于西方传统的超感性世界。
在康德看来,从有限的感性世界,通过艺术创造,跳到无限的超感性世界,就是达到了自由。
席勒更进一步提出了审美意识是既不受感性物欲限制又不受理性法则限制的“自由活动”的论断,并认为只有此种“自由活动”的人———“审美的人”———才是“完全的人”。
席勒把美之为美在于自由(超欲念功利)的观点提升到了整个西方近代意识的最高峰②。
从总体上来看,西方近代美学,基本上是以感性显现理性为美,把自由放在超时空的、超感性的王国,于是造成了美和自由的抽象性。
西方现当代美学反对这种传统的审美观。
海德格尔的“显隐”说,就是这种反传统观点的重要代表。
“显隐”说认为美和自由不在于超越时空、超越感性,而在于通过和超越时空之内的、当前在场的东西,显现出(实系一种暗示)同样在时空之内、然而不是当前在场的东西。
这里的超越不是古典美学所讲的超越到抽象的概念世界中去,而是从此一具体的领域(包括感性与理性的具体统一物)超越到彼一具体的领域中去,只不过前者出场(在场),后者未出场(不在场)而已。所以,此种超越就是由“显”见“隐”,即通过显现于当前的东西,显现出隐蔽在其背后、作为其深层根源的东西。审美意识就是通过想象的途径,超越到无穷尽的隐蔽的领域,此即艺术之所以能创造出一个令人玩味无穷的全新世界的原因。“全新”者,隐蔽的东西被全部敞开之谓也,亦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去蔽”。西方现当代的“显隐”说,与中国刘勰“隐秀”说所讲的意在词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思想颇相类似。
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象”说,也是讲的“美在象外”之意,亦即通过在场之“象”,显现(暗示)未出场的、隐蔽之“意”。西方现当代的“显隐”说和中国古典的“意象”说、“隐秀”说,都不是要创造一个超时空、超感性的抽象世界,而是要创造一个同样在时空之内的、具体的然而又是全新的世界。这是两者的共同之点,只不过在西方早有追求抽象概念王国的思想传统,故西方现当代美学在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时需要加倍努力,做一些反传统的工作,而中国则是“意象”说、“隐秀”说的传承至今不衰。西方由追求抽象的概念王国的美学思想传统到现当代“显隐”说的转化,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由自由的抽象性转化到自由的具体性。集西方传统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哲学,最典型地表现了西方传统美学所追求的自由的抽象性。
黑格尔把艺术、审美列为他哲学体系的无限性领域中的最低阶段,强调哲学所讲的“纯粹概念”是其最高阶段,他主张“结束艺术”而进入(中经“宗教”阶段)“哲学”,其根本理由就是艺术具有感性具体性,而仍带有限性,因而不够自由,只有最终达到了“纯粹概念”,才有最充分的自由。最抽象的领域就是最自由的领域,因而也是最高的领域———这就是黑格尔的审美观和自由观。黑格尔哲学垮台以后,西方现当代哲学、现当代美学的总趋势是由抽象走向具体:人的主体不单是理性的主体,而更是包括感性、欲望、本能、下意识等等在内的主体。
单纯理性的主体是苍白无力的,包括感性、欲望、本能、下意识等等在内的主体,才是活生生的,因而也是真正自由的。西方后现代艺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对此,我在其他论文中多有论述,兹不再赘。这里需要着重阐明的是艺术创造亦即审美的“去6蔽”活动所创造的全新世界何以是真正自由的本体论根源。
二、艺术的本质在于进入神圣的“澄明”之境天地万物本是各不相同而又彼此相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支持)的一大有机整体,人与他者(他人、他物)亦本互相融通,无有间隔。中国传统哲学所谓“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就是讲的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这种本然状态。但自从人有了自我意识之后,人与他者的关系就不再是平等共处和互动的关系,而为一种主体与客体二分的关系,即“对象性关系”:每个人都把自我当作主体,而把他者当作客体———认识和使用的对象。人与他者于是分隔开来了,所谓“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陆象山《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语录上》)是也。“限隔”就是限制—约束,人为了自我的生存而认识客体、使用客体,其结果是同时受到客体的限制—约束而失去了自由自主。求自我生存而同时丧失自由,这一悖论是人生不可逃避的必然,也可以说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常态。海德格尔称此种一般人的常态为“沉沦”(Verfallen),由于此常态是人生之必然,故又称为“必然的沉沦”。但海德格尔认为“沉沦”中的人既然是受“人”束缚的、不自由的“丧己”之人,那么,“沉沦”就是一种“非本真状态”(Uneigentlichkeit)。海德格尔主张人应摆脱“非本真状态”,返回到“本真状态”(Eigentlichkeit)③。什么是“本真状态”?如何进入“本真状态”?海德格尔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本来浑然一体,人若能从天地万物之无限整体的角度,而不是从具体有限事物的角度看待生活、看待事物,那就叫做“超越”。海德格尔又称此种“超越”为“无”。
“超越”是“对整个现实存在的克服”,“对现实存在的超出”④。
“超越”并“不脱离现实存在”,而是对现实存在采取一种超然物外、泰然任之(Gelassenheit)的态度,此种人生态度使人既不脱离现实,又能摆脱“欲求、异化和自我束缚”,达到一种不依傍他人、不为外物所累,一句话,超脱功名利欲的自由境界,此即回复到了“本真状态”⑤。
“本真状态”似乎是一种婴儿状态,“复归于本真”似乎相当于老子的“复归于婴儿”。
但完全恢复婴儿状态是不可能的。
老子的“复归于婴儿”也只是以婴儿比之,实系一种超越“欲”和“知”的“若愚”状态。
同样,海德格尔的“复归于本真”之“复归”,也当然不是回复到完全“无知”、“无欲”的状态,而是指一种超越上述主客二分和“对象性关系”的自由境界。此境又称“澄明”。海德格尔的“澄明”、“无”、“超越”之说,为康德、席勒的“美在自由”,找到了本体论根源。抽象艺术的鼻祖、俄国画家康定斯基认为,“艺术的精神”把人的精神从“外在的东西”中“解放出来”而“达到自由”。艺术创造不计较他人的“认可”或“不认可”,只听从自我的“内在需要”,像儿童一样,“因有赤子之心”而“与实用性无缘”,这样,画家才能以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新鲜目光观望一切”,画出有创造性的艺术品。康定斯基的这些话告诉我们,艺术创造的本真状态的自由境界,就是一颗赤子之心。海德格尔曾以面临死亡无之“畏”来描述这种自由境界,虽亦有深意,但不足为训。晚期的海德格尔则和康定斯基相似,也以艺术创造来回答如何进入此境的问题。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其论述比康定斯基更富哲理性。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质(亦即诗)是把日常生活中被分割、限隔的存在者带入天、地、神、人聚合为一的、敞开的“澄明”之中,从而显现其本真,人用诗的语言,言说着这四者的不同而相通的统一性,在此统一体中,不同的万物“相互隶属”,每一物都因其所属而成为该物,这是一种不同而和的统一体。海德格尔用“Ereignen”一词以表示这种相互隶属。人通过艺术创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神圣性7文艺研究2010年第181期期造,通过诗,而进入这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全新世界—一个“去蔽”了的、敞开了的澄明世界。
在此世界中,日常生活中的某物———一个壶、一座桥或农夫的一双鞋———与人的关系都不再是“对象性关系”,而是“真正人性的关系”:某物不再是人的对象,不再是被人认识、被人理解的对象,不再是“实现人的意图的材料”,而是在与万物一体的一体中被看待。
人在用此种眼光看待某物时,人才算是本真地作为人而诗意地栖居。
诗———艺术的本质,是人生进入“本真状态”的自由境界之源。
这种“进入”,为前所述,是一种“复归”,一种高一级的复归。
如果把美狭义地看成只是声色之美的外观之美,把美学狭义地界定为只是对此种愉悦之情的研究,那么海德格尔这里关于进入“本真状态”的自由之境的途径,关于诗的创造功能的讨论,便远远越出了美和美学的范围。
我倒是愿意把此种自由之境,叫做“心灵之美”,以别于表面的、浅层次的“声色之美”。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照亮每一事物的“澄明”是“神圣的”。
“澄明即定位,独自就能使万物各得其所”。
“澄明”使“每一事物都自由徜徉着”。
“澄明是最高者”,“澄明将每一事物都保持在宁静和完整之中。
澄明…是神圣的。
对诗人来说,‘最高者’与‘神圣’是同一个东西,即澄明”。
“澄明是欢迎之源,即神性之源。
”⑦海德格尔的这种种说法,都表明一个意思:艺术的本质(诗),使人进入澄明之境,而澄明是照亮一切事物之所是、之本真的最高源头,故它是神圣的。
“神圣的”一词是相对于日常生活的功用境界而言的。
日常生活,特别是现代技术化,把任何事物(包括人)都“对象化”,人的世界变得千篇一律,这样的世界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白天”。但这种“白天”在海德格尔看来是扼杀了人的本真,人的自由的“黑夜”,这样的世界是“不神圣的”。艺术的本质在于使人从“不神圣”的日常生活“突然地”进入一个全新的“神圣的”领域(艺术作品所揭示出来的领域)。试举一座石建筑的希腊神庙为例。石之本性在于“顽”(坚硬、沉重、块然、粗蛮等等),其可用性、服务性,如制成石斧供人砍物,是人强加于它的,不足以表现石之“顽”性。
与日常生活用科技对待石的情况不同,石在艺术品中,例如一座石庙(作为一个艺术品)之石,就“显现了在它上面肆虐的风暴的威力,同时,又在其对风暴威力的抗拒中”“显现了石之沉重和自我支撑”的本性—“顽”性。另一方面,石之“顽”性通过石庙这一艺术品,敞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石的光彩和闪烁使白昼之光,天空之宽广,夜之黑暗第一次出现。”天空的空间原是不可见的,但“石庙之矗立却使不可见的空间成为可见的”。这就是说,顽石一旦进入了艺术品,就恰恰由于其“顽”而显现出一个全新的生动具体的景象———“世界”。
按照通常的看法,石头的光彩和闪烁是“由于阳光的恩赐而放射出来的”,是先有天空、白昼、黑夜等自然现象,然后才有作为艺术品的石庙之光彩和闪烁,但海德格尔却更进一步看到了,在没有艺术创造之前的天空、白昼、黑夜是“不可见的”(抽象的),只是有了作为艺术品的石庙之后,才使天空、白昼、黑夜成为具体“可见的”。
同理,雕刻的神像,作为艺术品,就比神的肖像更能显现神之本然。“正是石庙之矗立,才第一次给予事物以神色,给人以对其自身的看法。”这就是说,只有艺术品才照耀出万物之本然,使万物得以“升起”、“发生”。艺术创造的“神圣性”,从海德格尔所举的石庙这一例子中,得到了十分形象的说明。
三、“生活的艺术化”在于以艺术的神圣之光照亮生活艺术,一般来说,总是与艺术品相联系,具有声色之美。
但在把美的内涵由视听的感性美延伸为心灵的自由,更进而像海德格尔那样追寻到自由的本体论根源,把艺术的本质归结为神圣的“澄明”之后,艺术就不仅与艺术品相联系,而且很自然地可以进而与人的生活相联系,8艺术、审美可以扩展到人的生活了,这就是“生活艺术化”或“生活审美化”。
生活艺术化有低层次与高层次之分:低层次的“生活艺术化”是指生活用品的艺术化,生活环境的装修,以至人体的化妆之内,所有这些显然还与物质、功用、消费等等密切相关。
但还有更高层次的“生活艺术化”,这就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具有内在的心灵之美的艺术化生活,我以为这也就是进入海德格尔所谓“澄明”之境的生活。
只有当人的生活达到了“澄明”之境,为“澄明”所照亮,这种生活才是真正艺术化的生活,生活本身成了艺术品。
此种心灵之美显然不是表面的声色之美可以涵盖的,它是生活之美的核心和灵魂。
西方后现代艺术所倡导的“生活艺术化”,特别是所谓“行为艺术”、“身体艺术”之类,也许就是上述艺术观或审美观不断延伸和深化的体现,尽管现当代某些“行为艺术”、“身体艺术”只是在表面上表现生活的艺术化,而丧失了艺术之心灵美的本质。
海德格尔本人并未像后现代艺术之父杜尚那样做到生活的艺术化,但他的艺术理论实际上为后现代的“生活艺术化”奠定了基础。
海德格尔艺术理论的核心,为前所述,是超越日常生活之功用性,敞开一个“澄明”之境,这“澄明”就在于体悟到万物各不相同而又“相互隶属”、相互融通为一整体。
以“澄明”的眼光看物,物非人使用的对象,而为艺术品;以“澄明”眼光看人,则人亦非被我使用的对象:人与人不是相互利用,相互限隔,而是因“相互隶属”,相互融通,从而相互尊重。
我隶属于他人,故我尊重他人(的“自我)”;他人隶属于我,故他人亦尊重我(的“自我”)。
处在这种人际关系中的人,就是进入“澄明”之境的人,其生活就是为艺术的神圣之光所照亮了生活。奥地利犹太裔宗教家、哲学家马丁·布伯,从宗教的角度,用宗教的语言,论述了这种生活的神圣性。布伯没有运用“艺术”、“审美”这样的字眼,但他的观点完全适用于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布伯根据人的生活态度,把人的“生活世界”分为两重:“被使用的世界”(the world to beused)和“相遇的世界”(the world to be met)。布伯用“我—它”(I-it)公式称谓前者,意即自我把他者(不仅指物,而且指人),当作“物”来使用。布伯用“我一您”(I-Thou)公式称谓后者,意即自我把他者(不仅指人,而且指物)当作神圣的、大写的“您”来看待。布伯是一个宗教家,他把“我—您”的关系看作是人与上帝的关系的体现,这是人性中的根本,布伯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已经失去了根本,他极力主张恢复人性之根本,要求承认“我—您”关系在人生中的首要地位。“人生并非只是在及物动词的领域里度过的,并不只是依靠以某物为对象的活动才存在着的。我知觉某物,我想象某物,我意愿某物,我感触某物,我思考某物。
人生并非仅仅在于这一类的东西。所有这些只构成‘它’的领域。”而在“我—您”关系中,“当说到‘您’时,言说者并没有把什么物当作他的对象”輥輰訛,而是把“您”当作“能做出自我决定”的“有自由意志”的人来看待的。人皆有“自我性”(独立自由的主体性)。
布伯所谓有“自由意志”的人,实即我们一般所谓人的“自我性”,布伯所要求的实系尊重他人(布伯的“您”)的“自我性”。在布伯看来,人的“自我性”具有神性,犹太人就是以“您”来尊称上帝的。人的“自我性”,在布伯看来,是“真实生命的摇篮”。那种把他人当作物一样来看待,当作满足自我的欲望或期望的目标,当作实现自我之私利的工具的人,是不能和他人“相遇”的。所谓“相遇”,也就是不夹杂功利的隔阂,两人在灵魂深处直接见面,也就是赤诚相见。
布伯特别强调“相遇”中双方的相互回应。在日常功用的世界中,只有我对他者(“它”)的主动作用,他者(“它”)完全是被动的,没有回应,故两者隔阂;反之,在“相遇的世界”中,双方互相回应,构成“我—您”的一体。布伯的“一体关系”颇像我所说的“不同而相通”的“万物一体”。布伯的“互相回应”,源于彼此“相通”。“相通”才能构成整体—“一体”;在“我—它”的使用世界中,彼此不相通,不能构成“一体”。布伯的“一体”关系由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神圣性9文艺研究2010年第181期期于上帝的光照而形成,是一种宗教情绪,但也具有中国人所讲的“万物一体”的诗意,我把布伯的“我您一体”的关系解读为审美情绪,与海德格尔的“澄明”相似相通,也是一种艺术的神圣之光,它能照亮人的生活,使人的生活艺术化。布伯说:“一切真实的生活乃是相遇(All realliving is meeting)。”达到“相遇”(不仅人与人“相遇”,而且人与自然物“相遇”),就做到了人的生活的艺术化。
四、中西两种不同的“生活艺术化”在西方,“生活艺术化”本是后现代主义为反对现代艺术片面重少数精英艺术、重声色的感性美、重理性和科学的产物。
但后现代的艺术生活化,在我看来,却产生了高低两个层次的审美观和艺术观:一是把生活艺术化简单化、表面化为大家谈论的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生活用品的艺术化,消费品的广告宣传,生活环境的装修,人体的化妆等等。
此种“生活艺术化”,特别是其中的低俗之风的结果,是把本来与物化、功用化相对立的艺术化变成了物化、功用化,反而扼杀了自由,扼杀了艺术的解放功能。
这种弊病的关键在于把艺术降低到日常生活的水平,而不是提高日常生活的精神境界,把艺术降低为审美的低级形式,甚至降低到动物的低等审美形式,以致肉欲横流。
此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已遭到德国当代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等人的大力批判,我国许多美学学者,结合我国社会上所出现的此种现象,也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此种现象的弊端,本文不拟在这方面多所论述。
我这里只想申述的一点是,我们倒也不必简单否定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必简单否定这种艺术化的活动。
特别是我国当前社会上所热衷的种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前片面讲革命而压制生活的一种反作用,值得谅解。
重要的是提高日常生活的精神境界,让商品的艺术化、生活环境的装修、人体的化妆等等都渗透着人生高远的精神境界。
现在社会生活中许多低俗现象,来源于高远的精神境界的缺失,我们应当加强这种种活动背后的人的审美教育。
这就涉及后现代“生活的艺术化”的更高层次。
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我在其它论著中已有论述,这里倒是想简单重述一下后现代艺术之父杜尚的艺术生活的例子,因为他的名言最能说明“生活艺术化”的深层含义:“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
杜尚生活的前期虽然作画,但出于他个人“对抗感性美”的“潜意识”輥輵訛,其画作的特点是根本没有感性美。
例如他的名画《从处女到新娘的变迁》,完全没有视觉上引起性感的肉体形象,尽是些机械般的线条,把人画成了“机器人”,然而这幅“机械画”,却把一般人羞于谈说的人生旅程中最神秘的一幕,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观众从这里所欣赏的,完全不是视觉美,而是对人生的领悟。
这里的美,不属感性美,而是一种思想美。
杜尚的画作不在意悦目,而在于展现他生活的思想境界。
“艺术为思想服务”,这是杜尚生活艺术化的具体内涵。
杜尚的思想,是对西方那种非此即彼的重分别、分析的理性至上主义传统的反抗,他认为这种理性至上主义压制了自由。
他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提倡一种亦此亦彼、彼此融通、相反相成的思想,有些类似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易老之学的阴阳合一。
又如他的另一幅名画《门》,就是把“开”和“关”两对立面合而为一思想的体现。
杜尚生活的晚期,其生活艺术化的思想甚至进一步发展到干脆放弃绘画,让他的生活本身成为他所说的“最好的艺术作品”。
杜尚为人,超然物外,淡泊名利,尊敬他人,乐于助人,周围的男男女女都很喜爱他。
杜尚潇洒超脱的生活本身,为“澄明”的神圣之光所照亮,属于“我—您相遇”的“最真实的生活”,的确体现了艺术的本质:自由,是“最好的艺术作品”。
就“生活艺术化”的实质内涵而言,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谓古已有之。
庄子妻死,鼓盆10而歌,可以说就是超脱了生死大限而进入了一种艺术的自由之境,用西方后现代艺术的语言来说,算得是一种“行为艺术”,而且是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行为艺术”。
庄子的庖丁解牛,也是一种顺乎自然规律而达到自由之境的“行为艺术”。
魏晋士人,其言行举止,大都展现了潇洒自由的神采和风姿,真的是一种“生活艺术化”。
如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其“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晋书·阮籍传》)。
刘伶虽“形貌丑陋”,然“肆意放荡,悠焉独畅。
自得一时,常以宇宙为狭”(《世说新语·容止》)。
魏晋士人所崇尚的这种种“生活艺术化”的人物风格,皆其自由境界之体现,究其社会历史根源,盖由于对汉武帝以来思想统治之反动。
汉武帝用董仲舒策,独尊儒术,个体性自我从此被湮没于三纲五常、贵贱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群体之中。
魏晋人士上述种种“艺术化”的生活姿态,一言以蔽之,皆在于“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欲摆脱各种封建社会群体之束缚而求得个性之自由、解放。
如果说西方后现代所宣讲的生活艺术化,是为了自由而反对西方理性至上主义之类的传统束缚,那么中国古人所践行的生活艺术化,则是为了自由而反对中国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对个体性自我的束缚。
西方后现代艺术所追求的审美自由,是在文艺复兴已经让个体性自我从封建神权统治下获得解放而独立之后,要求自由的进一步深化;而中国从魏晋士人开始所追求的审美自由,则远远落后于西方,此种自由还只不过是要求从封建统治下获得个性解放,要求个体性自我从封建社会群体的湮没中脱颖而出,从而获得独立地位。
在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追求审美自由的历程,既漫长,又艰苦,甚至惨烈:其结局或归隐田园,或就囹圄,惨遭屠杀。
嵇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
……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晋书·嵇康传》)。
然嵇康公开揭露统治者“矜威纵虐”,批判儒家名教的虚伪,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致为统治者所不容,惨遭杀身之祸。
嵇康下狱时,“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是豪俊皆随康入狱”(《世说新语·雅量》)。
临刑,“太学三千人请以为师”(《晋书·嵇康传》),而“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三国志·魏志》注引)。
临刑援琴,何等惨烈悲壮的“艺术”人生!何等崇高豪迈的“审美”境界!陶渊明的艺术化生活是另一翻景象。
陶渊明第一次为官,就“不堪吏职”,深感“志意多所耻”,于是“少日自解归”。
最后一次为官,任彭泽令,仅三月,又因不甘“为五斗米折腰”而赋《归去来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所谓“以心为形役”,就是湮没自我于宦途,为功名利禄所束缚。
迷途知返,归隐田园,就是为了越名缰利锁而进入自由的境界。
《归田园居》:“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
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自复归田园以后,如鸟脱樊笼、复返自然的艺术化生活,深切而生动地表现了他抱朴含真的审美自由境界。
“此中有真意”之“真意”,与海德格尔的“本真状态”相似相通;“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与布伯的“我—您相遇”可以互相辉映。
中国的封建专制和思想统治的历史,自汉武以后,一直延续不断,至晚明而愈演愈烈。
晚明的大思想家李贽则是一个为反对封建专制和思想统治而用自己的生命、身体来实现自我之自由本质的悲剧性人物。李贽福建泉州人,二十六岁中举,三十岁初仕,任河南辉县县学教谕。
五十二岁任四品姚安知府,五十四岁离任告归后,潜心著书,设壇讲学,听众“一境如狂”,因不满黑暗统治,屡遭污蔑,六十二岁削发为僧,由于正道直行,遭官府迫害,七十六岁被捕入狱,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神圣性11文艺研究2010年第181期期在狱中自刎。李贽强烈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答耿中丞》)“虽孔夫子,亦庸众人也。
”(《焚书·答周柳唐》)“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
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
虽使孔夫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以据以定本行罚赏哉!”(《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李贽以反孔闻名,并非反对孔子的一切言论思想之本身,其本意在于反对定孔子为一尊,一切依傍孔子而无己见。“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以为真可笑矣”(《焚书·答耿中丞》)。由此观之,李贽反孔之思想主旨在于反对“舍己”,亦即反对惟他人残唾是咽之人,反对丧失自我的自由本质之人。李贽为人、为文,惟摅其胸中之独见,劝人力戒言不由衷,说“伪言”,行“伪行”,做“伪人”,他要求人吐“真言”,行“真行”,做“真人”。他认为人皆有本然之心,伪道学使人心蒙上尘垢而失其本然,乃“真心”之障碍。“夫童心者,真心也,绝伪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焚书·童心说》)。李贽斥责伪道学先生之“伪”:“口谈道德,而心在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侯》)。与伪道学先生相反,以李贽本人虽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官至四品,仍然学陶渊明,辞官归里。究其“本心实意”,在于不因富贵而屈于人,在于“一念真实,受不得世间管束”,与陶公“偶与同耳”(《焚书·豫约》)。
李贽如此超脱功名利禄的“世间管束”之“真心”、“童心”,是他以“游于艺”为人生最高精神境界的人生观、审美观的体现。至于他最后出家为僧的行为,则更彻底地表现了他不受世间管束之“真心”、“童心”,也是他“游于艺”的人生观、审美观的更深一层的表达。削发为僧,应可称为对世俗、功利—“世间管束”的一种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是消极的。李贽之死,是他追求自由的一生的悲剧性的总结。李贽以“妄著书”、“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入狱,狱中仍做诗读书自如。一日忽持剃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袁中道《李温陵传》)。
李贽死后,其著述被视为“异端之尤”,下令“尽行烧毁,不得存留”。然“卓吾死而书愈重”,其著述更广为流传,以至远及外洋。李贽不过一介书生,著书立说,“其意大抵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其为人也,“绝意仕进”,“狷洁自厉”(袁中道《李温陵传》),“不蹈故袭,不践往迹”(《焚书·与耿司寇告别》),奋不顾身,一往无前。
其“所求”者何?非功名利禄也,为不受“世间管束”之自由故也,为做“真人”之故也。不自由,勿宁死。
李贽不仅是一般为自由而死之“真人”,而且是出自他的自由意志,在面临死亡中体悟人生的自由本质之“真人”,就像海德格尔所谓面临死亡而“返回本真状态”一样。
用西方后现代“生活艺术化”的语言来说,李贽的生和死,都是最好的、最深刻的“行为艺术”和“身体艺术”。而且他不是表演给观众看的,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绘制成的。
杜尚说他的生活就是他的最好的艺术作品,李贽也是一个以自己的生活来表现和创造自己最好的艺术作品的人,不过杜尚的生活作品是潇洒自在,而李贽的生活作品是惨烈悲壮。
这种差别是由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背景造成的。
西方后现代艺术化的生活,特别是“行为艺术”和“身体艺术”,是用生活中的行为和身体来表现自我的自由本质的艺术,如前所述,它是适应文艺复兴已经让自我的个性获得解放而独立之后,人们对自由有了更进一步的更深入的要求而产生的,杜尚生活作品的潇洒自在是此种自由的表现,他也无需为他的生活自由付出什么代价。
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使中国12历史文化长期处于湮没自我、湮没个性的阶段,故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化的作品必须为摆脱封建思想统治的传统桎梏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李贽的生活作品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虽在晚明,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根据以上关于中西两种不同“生活艺术化”的对比,我以为:西方当代人的“生活艺术化”,有待于进一步超越传统的非此即彼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生活艺术化便放弃绘画,为了艺术服务于思想便放弃感性美,甚至生硬地制造一些非正常生活的“艺术化”生活。
针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我以为我们的“生活艺术化”的关键在于提高人的心灵美,重在一个“真”字,像李贽所主张的那样:吐“真言”,行“真行”,做一个“真人”;由此而建立的美学体系应在阐发“美在自由”的思想和命题方面下功夫。
如果像《论语·为政》所讲的求官之道(“学干禄”)那样,“言寡尤,行寡悔”;像《论语·乡党》所教导的那样,见“上大夫”是一个姿态,见“下大夫”是另一个姿态;进入朝廷的门,就要像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自己容身的地方一样(“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经过君王的座位(“过位”),连话都像说不出来(“其言似不足者”);“升堂”,憋着气似乎不能呼吸(“屏气似不息者”)……总之,言不由衷,行不由己,那还谈得上什么“生活的艺术化”!谈得上什么建立新的美学体系!
- 认准易品期刊网
1、最快当天审稿 最快30天出刊
易品期刊网合作杂志社多达400家,独家内部绿色通道帮您快速发表(部分刊物可加急)! 合作期刊列表
2、100%推荐正刊 职称评审保证可用
易品期刊网所推荐刊物均为正刊,绝不推荐假刊、增刊、副刊。刊物可用于职称评审! 如何鉴别真伪期刊?
都是国家承认、正规、合法、双刊号期刊,中国期刊网:http://www.cnki.net 可查询,并全文收录。
3、八年超过1万成功案例
易品期刊网站专业从事论文发表服务10年,超过1万的成功案例! 更多成功案例
4、发表不成功100%全额退款保证
易品期刊网的成功录用率在业内一直遥遥领先,对于核心期刊的审稿严格,若未能发表,全额退款! 查看退款证明
其它热门杂志征稿信息
发表流程

排行榜
- 推荐
- 点击
投稿百科
写作指南